胡晓明:《花溪集
妻生日忆及二十一年前新婚题词惠而好我携手同行遂以居家散步之地布帛菽粟之味杂写为叙以寄芳辰二十六韵
某馆长问事于余猛忆有商家昔曾邀余加盟一古籍项目允敝馆约二十余种精善本再印或已面世矣惊梦一场颇释然转念及藏固安稳印亦欣然戏得一绝以记之
邓小军教授撰文永王璘案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踏勘江西南昌永王墓得句满村能说璘名字感赋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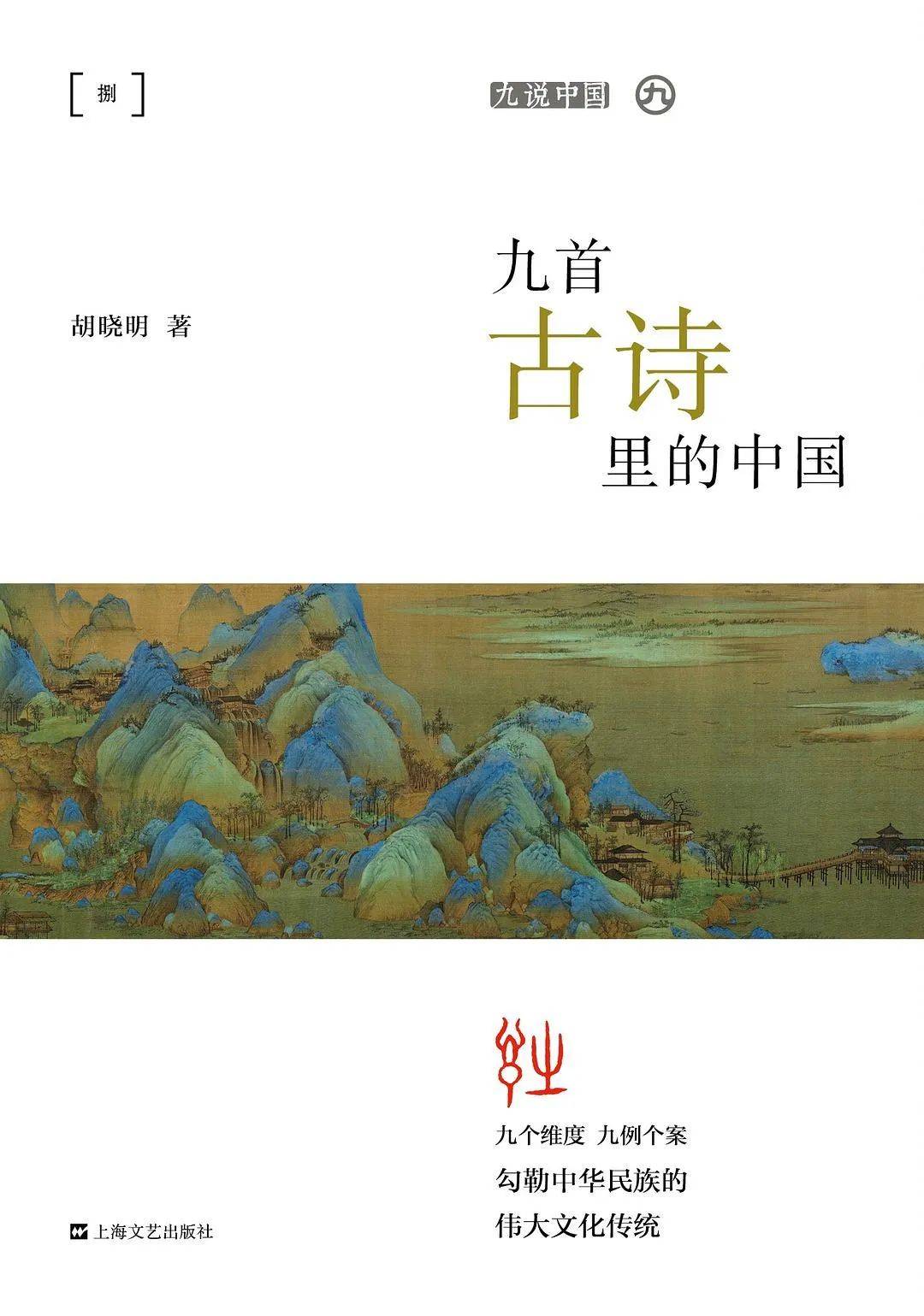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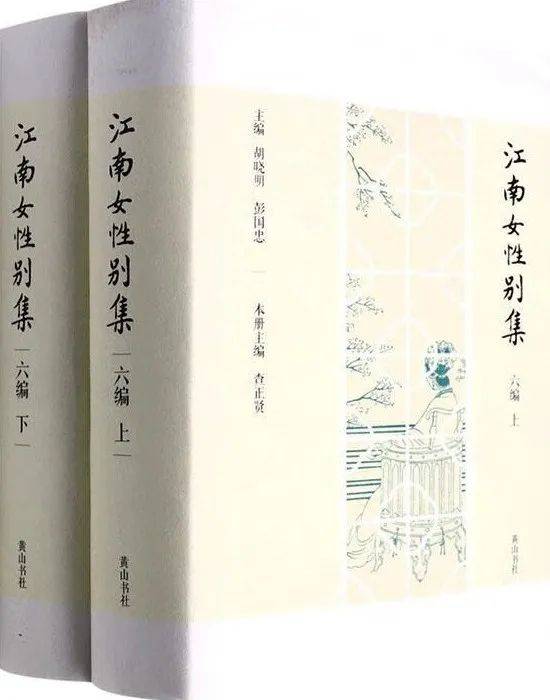
丁酉年夏,余再返花溪,于孔学堂驻园研修。十里河滩,处处山岚静秀,溪河碧清,日日宛如画中游矣。稼轩语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如何不负青山,亦不负我心,研读典籍之暇,游心岚翠之余,唯以随笔文字,聊记种种如次。
余晨起练太极,静思默想之间,于草叶树叶,偶有会心。细看周遭种种未名草木,其叶形,或圆或长,或纤或扁,有妍有丑,形状万千,然皆向上、向外,向阳、向天,无一或异。
可悟大千世界,种种存在,各美其美,竞态极妍,然皆向外求发展、求资源、求阳光与空气,更求表达、显能、扬己,故争取资源,表现自我,无疑为生命之第一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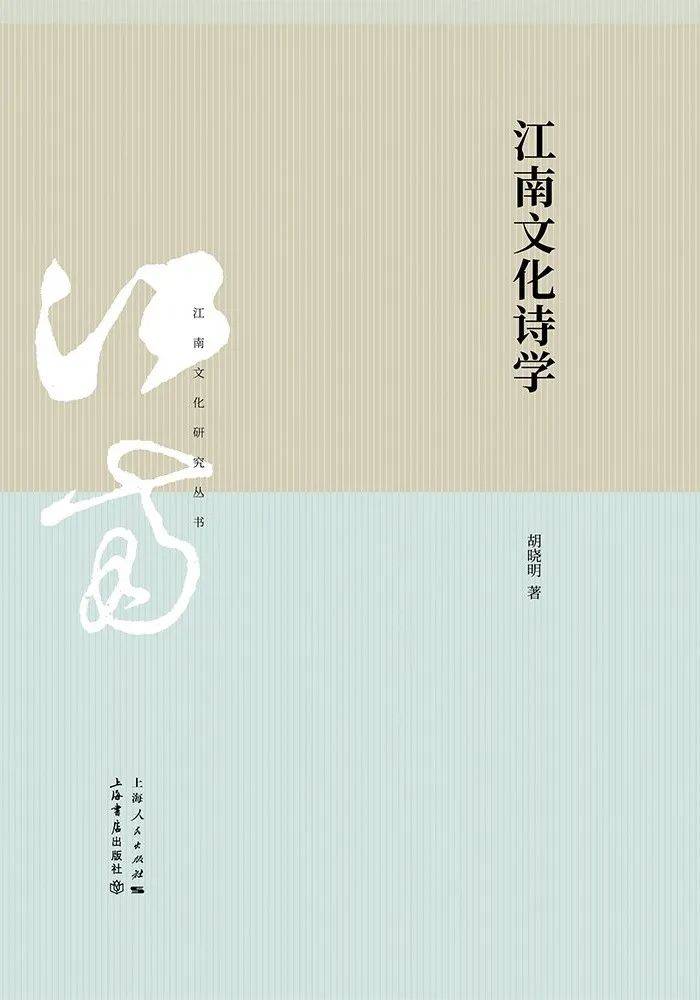
然大自然之中,亦似有一无形之手,将万千形态之草木,各各安排,或低或高,或单或簇,旁见斜曳,妥帖停当,无乱象、败象、争斗相,或圆或纤,或妍或丑,皆能从容而自得,以遂其生机,古人所云“万象森然”“冲漠无朕”,朱子所谓“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细思此事,终不可解也。
孔学堂位于十里河滩之中部,南北两翼,青山如螺,绿树如鬓,溪河如带,无数漫滩、沼泽、水田、花圃与湿地,如美人春衫舒展之长袖。余不可一日不见青山,亦不可一日不见此滩。常于昏旦之间,流连盘桓,于河滩看清波回旋,白鸟翩飞,听深柳莺啼,荷塘蛙语。河中沙洲、小岛、跌水、浮桥、不系之舟、亲水之亭,亦一一如数家珍矣。然此一大湿地,并非如是如是、自然原生之景观,而乃人力返自然之杰作也。
由此乃悟:老子之道法自然,非原始之自然,而实为以人类之自我忏悔、自我反省、自我醒觉,重经人类之力,而归返之“自然”耳,已与原生、野蛮之自然,非同一自然矣。人类由傲慢而谦卑、罪过而自新,即所谓“道法”,即现代性返本更化之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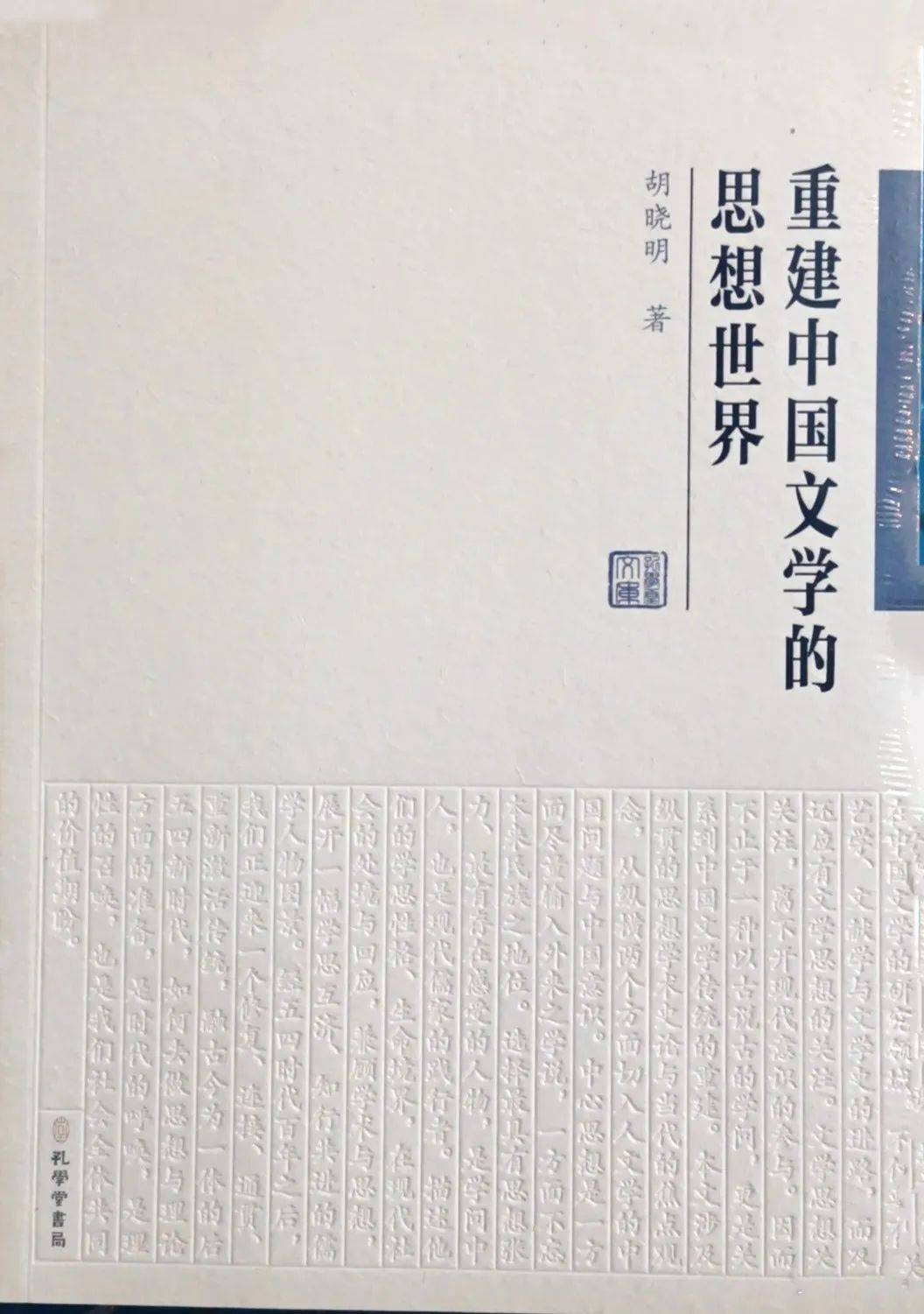
偶观扎克伯格于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之演讲。一如吾国王阳明先贤所言:“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扎氏之志与天理,即世界公民之理想、共享社群之建造、连接一切之努力、人人皆有存在意义之世界。矫健、俊逸、清新,生命之风姿直上直下,扑面而来,沛然莫之能御。诗可以兴,此即是可兴;诗可以观,此即是可观;诗可以群,此即是大群。余因之而有感焉:真诗乃发挥一己之智慧,体现人类之灵魂,表达时代之精神也。
上午与诸生讲“沦肌浃髓”。现代人之语文教育,与现代人之阅读,零碎而浅表,如写字于瓷砖,画符于沙滩,雨过如洗,潮去无痕,全无受用。
古典中国之阅读传统,讲求内在化,体用而引归身受,如朱子所谓“且将此一段反复思量,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使自会沦肌浃髓”。因而今日欲求读书生活之真谛,“沦肌浃髓”似不可不讲。要义有三:一曰超感官,二曰超逻辑,三曰尚气。直凑单微,打开活路,文学之人物、情思、意象,矫健、俊逸、清新,以生命之风姿,人格之光彩,觌体相见,莫逆于心,如古人所云“沦肌浃髓,而能养民于和,固亦有不春而温,不寒而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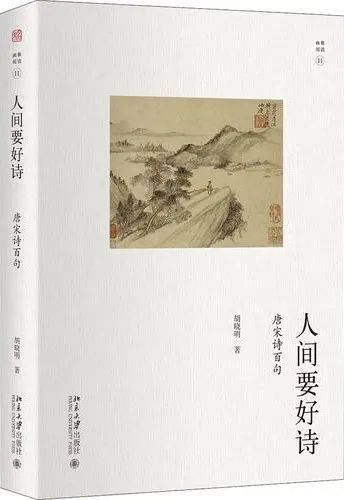
今日读钱宾四《中国史学发微》,此书论及人物之隐而不彰。如王船山于清初姓名若晦若失,其书亦隐沦不传,然数百年后于当时之思想,放大光彩、有大贡献云云。读国史当于此等处注意。口占一绝云:“粗识书中造化权,魂消风信百花前。探春诸友如相问,聚散虚空去复还。”
花溪之生活,夙兴夜寐,身心通透,节奏较沪上缓甚。如鱼戏于渊,鸟翔林间,可隐亦可显;如花开花落,莺啼虫鸣,无喜亦无嗔。散漫而有秩序,恍为葛天氏之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静观湿地生物之繁多,万类相生之自由,忽有思焉。庄子所谓“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自近代以来,国人渐脱于血统、政统、道统,即宾四先生之所谓“三统”,而相忘于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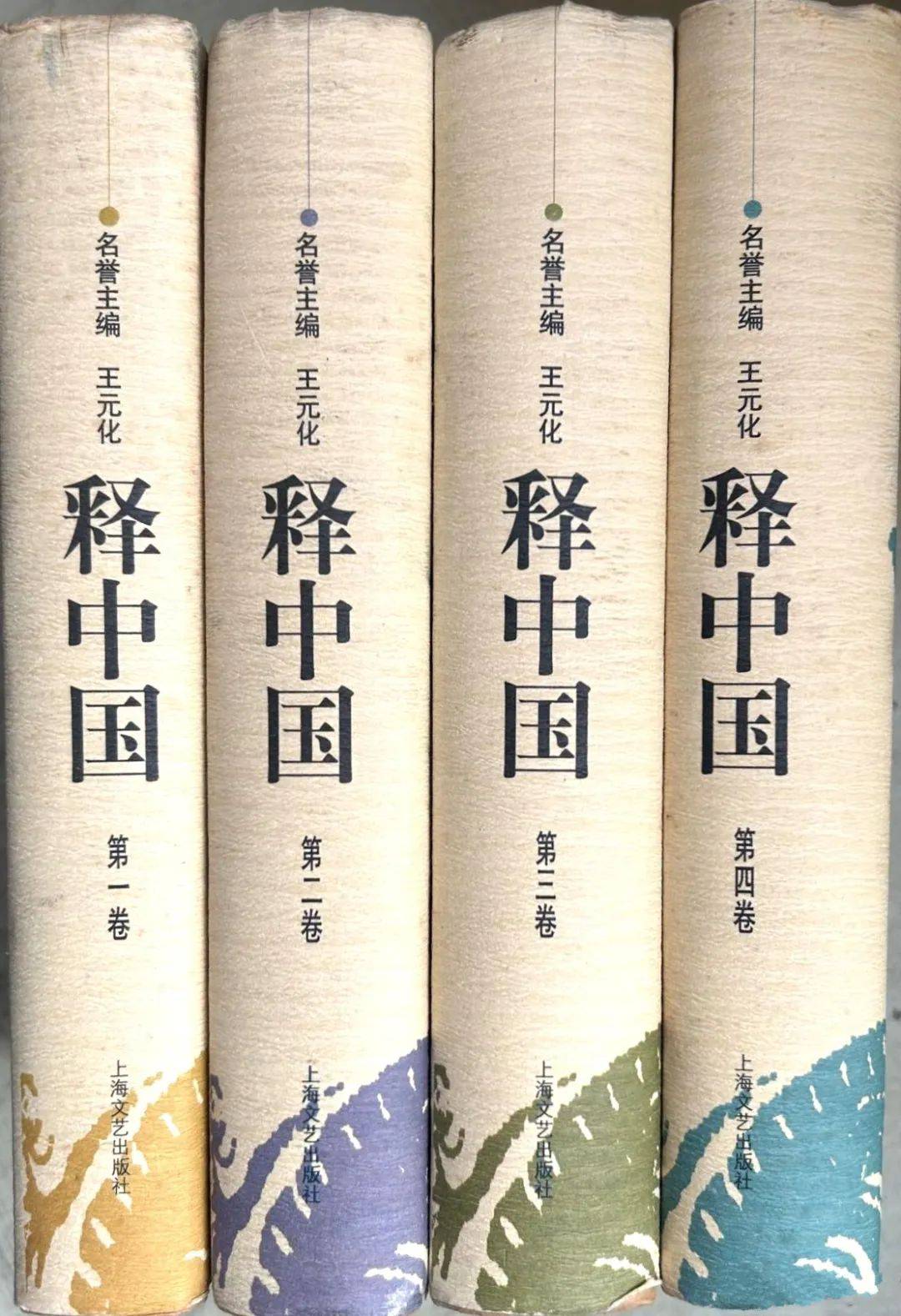
江湖即无群体、无边界、无限定、无现成、无束缚、无笼罩之状态,然现代人亦因此而寂寞、而空虚,无挂搭、无归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因而思返相濡以沫之涸辙耳。然此皆不知“江湖”之真义也。盖庄生玄理,其义甚圆。“江湖”之旨,须与“濠上”之乐对读。“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先须每一个体之生命,真有所安、真有所“乐”,方有江湖之“忘”矣。
而濠上世界,恰如当今之网络世界,万人如海一身藏,分众而共享,可出又可入,相忘又相呴,相分又相濡,此一大新江湖,正创造无数鱼之乐而不自知也。唐人诗云:“惠施徒自学多方,谩说观鱼理未长。不得庄生濠上旨,江湖何以见相忘。”(陆希声)噫!诗岂小道也哉?
馆舍窗前,有巨幅青山,浓翠如染,日日相对,令人百看不厌。滔滔孟夏,草木蒙笼其上,随风摇漾如醉;白云蹀躞山头,尽日苍狗幻化。时有白鹭翩飞,蜻蜓戏叶,鸟跃林间,蝉唱幽处。宋人唐子西氏所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亦不知斯世何世也。
半山有草轩,一翼如画。南北接一山间小径,以竹为栏,忽隐忽显。当其显时,轻柔为体,蜿蜒如带;当其没时,绿荫丛簇,神秘存焉。小径似有无穷意思,无端召唤,引余常临窗坐对,寂然无思,而身心两忘,神气独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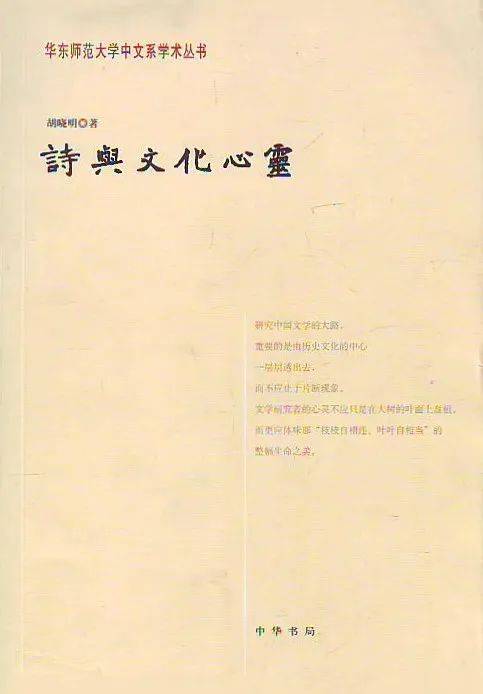
径与山,岂非亦隐喻天与人乎?余亦因此而悟:当其显也,轻着人力,顺承自然;当其隐也,混同物我,归于寂寞。老子所谓虚静柔弱者,神明之府也。现代人之不见天地之美与神明之容,唯甚与泰尔。
花溪之生活,又现代又古典,又西式又本土。如晨饮咖啡,而午后清茶;练毕太极拳,又聆爵士乐;一手拿手机眼看八方,一手持青瓷澄怀观道。一如王弼所谓“应物而无累于物”。
余读汤用彤先生书,彼认魏晋玄学高于汉代元气论。余以为不然。盖玄学主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然太极有太极之体,爵士乐有爵士乐之体,二体非一体也;手机有手机之体,青瓷亦有青瓷之体,二者亦各别为一物。然则古之所谓体用不二,何以不二?何以依体而起用,余亦不得其解也。余因而主张汉代之元气论,更高于魏晋之玄学论,此意非片纸能办,有暇将详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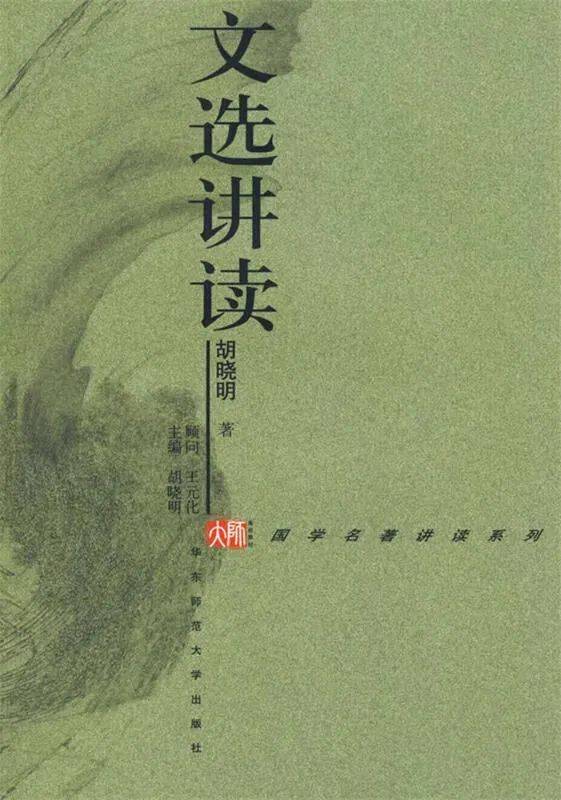
今讲中国艺术与美学之“疏野”。现代人厌倦文明之造作与繁复,返思古代社会之率真与朴野。然疏野一品,非懒散、粗野、鄙野、狂野、疏陋之谓也。
要义之一,即由文返野,如魏庆之《诗人玉屑》“诗要有野意”条引陈知柔《休斋诗话》云:“人之为诗要有野意。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陶诗之野意,乃由高贵与精致之功,九转灵砂而之成。
要义之二,疏野之背后,全幅是人生之存在状态,乃非城市、非权贵、非有为、非富贵、非秩序,凡有意之“反”,亦不疏野矣。所谓“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中国美学之概念,大都背后隐然有人焉。
为迎第四届东盟教育交流周,十里河滩管理方沿河驱赶钓鱼者。钓鱼者乃真疏野,可见今人造园林,皆假疏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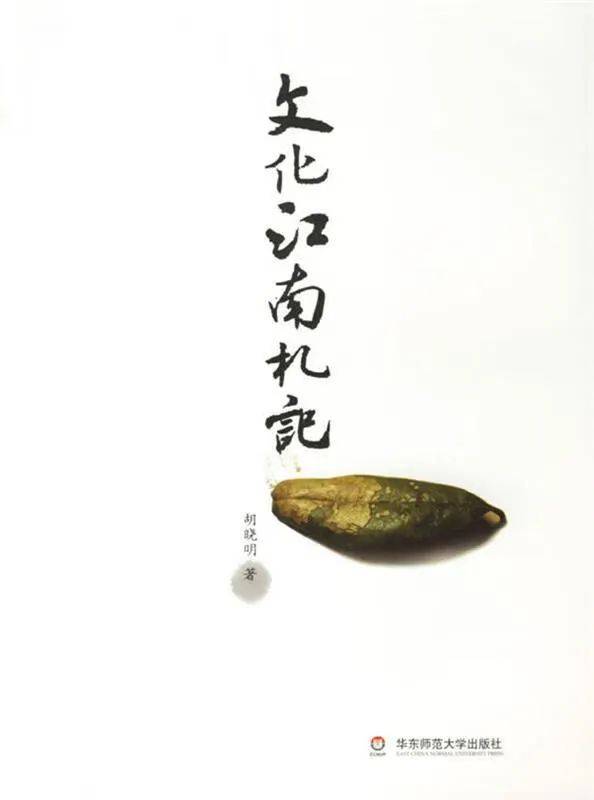
前四项,皆俗谛;后两项,高人也。王维乃诗兴之感发,世界自生自主,有超然物外之思。牛顿乃科学之妙悟,洞察幽微而寄心上帝。读书治学,应立足于高山之巅,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游心以远。此乃古今之贤人志士进德修业之大义也。
仲夏之夜,星空璀璨,大地沉平,深树蝉鸣,流萤时飞,余亦有所思也。顾积数十年之努力,余苦心经营,力图建立一整体之诗学,姑名之曰“中国文化诗学”。何谓也?
近现代以还,诗学散而为文献、笺疏、诗人、诗史、诗法、诗风及修辞,自守家法,各照隅隙,此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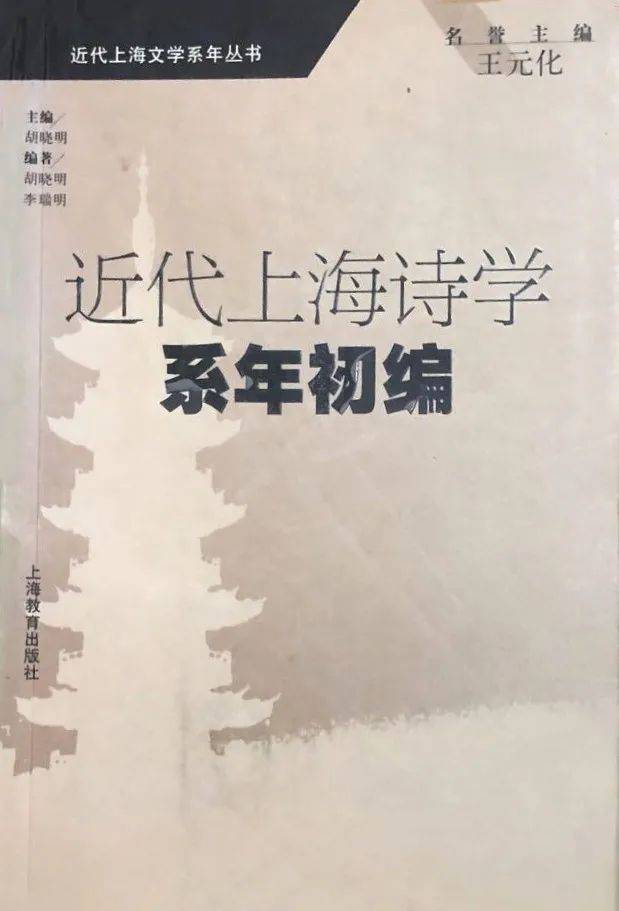
故吾之所谓“整体”,所谓“文化诗学”,于诗之外部而论,既扬弃古人,又反思现代,既庄情孔思,又聚焦诗艺。于诗之内部而论,力求地与人合,灵与智合,实与虚合。地与人合,即江南诗学之开展;灵与智合,即意象诗学之建立;实与虚合,即化理论而为现象,以小见大,以实涵虚,由个别见一般,如唐宋诗比较论、二柄诗论、今古典论等。
中国文化诗学之整体观,力图由现代道术之裂,上通生生之证、息息相关、上下相连之诗天地,以回应西学之偏胜与古学之偏枯,此境此义,乃灵魂之冒险,而经师宿儒与新潮论家,多未能梦见也。
花溪妙境,花开又花落,无喜亦无悲。唯日日启窗,不禁对山色青青,叹衰颜自我。余问青山,何时方老?青山问余,几时归来?遂作《忆花溪》八首。
胡晓明,四川成都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江南文学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著有《中国诗学之精神》《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诗与文化心灵》《江南文化诗学》《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饶宗颐学记》等,编有《释中国》《江南女性别集》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主题测试文章,只做测试使用。发布者:小编,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yingzhewang.com/dongcha/1905.html


